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代皇帝,于公元626年登基,共执政二十三年。他在位期间,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史称“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为唐朝的繁荣昌盛持续达三百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618年,李世民协同其父李渊建立了唐朝后,自己则为统一割据的局面和巩固唐王朝初建的政权,继续南征北战达八年之久。不少战马伴随着李世民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特别是其中六匹坐骑在几大关键战役中战功显赫,深为唐太宗所钟爱太宗不仅亲自赐予它们漂亮的名字,还撰写赞诗加以颂扬。公元636年,唐太宗选定九山营建昭陵,下令将它们勒石刻碑,与他永远相伴。六骏浮雕由当时充营山陵使、工部书、名工艺家阎立德(?-656)设计,著名画家阎立本(?-673)起草图样,由筑陵石工的高手雕刻而成。六块浮雕分东西排列两行,耸立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两边,遂成为千古迹--“昭陵六骏”。这些浮雕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一反当时传统的格式化的陵寝石人石兽和宗教艺术,开创了雕刻艺术的新气象,在中国雕塑史上享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昭陵六骏”任凭风吹雨打、朝代变迁,在陵园伴随唐太宗达一千三百年之久。二十世纪初却不幸被盗,历尽坎坷曲折,现其中四骏特勤骠、青骓、什伐赤、白蹄乌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两骏飒露紫和拳毛蜗已流失国外,现由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以下简称宾大博物馆)收藏。八十年来,对于两骏何以离开昭陵与中国,特别是两骏何以人藏宾大博物馆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众说纷纭。国内报刊杂志几乎曾无一例外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及宾大博物馆的掠夺行为,多少年来宾大博物馆为此也一直呼冤喊屈、竭力申辩。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宾大博物馆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直接接触,许多情况得以澄清,原谴责宾大博物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盗的昭陵六骏陈列说明现已改写。尽管如此,两骏人藏宾大博物馆的具体经过与宾大博物馆所掌握的六骏资料仍为众所不知,误解依然。笔者自1995年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特别注重两骏入藏宾大的经过。收集的资料和研究的部分结果已发表在香港出版的《东方》(Orientations)杂志2001年2月刊上。当时由于篇幅有限,仅作了简扼的介绍。现应碑林博物馆之邀,特将本人所收集的关于昭陵两骏流失的全部资料重新整理,纂成此文,希冀有助解开扑朔之谜,并促进对昭陵六骏的讨论与研究,以增进中美博物馆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正文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宾大博物馆的创建史和与两骏入藏宾大博物馆有关的几位关键人物。
一、宾大博物馆与卢芹斋
费城曾是美国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中心,在十八世纪时是北美洲最大的城市。这里政治家、教育家和实业家云集,他们思想开放,开拓创新,富有远见,热心于教育与公共慈善事业。1794年,本杰明•兰克林在费城创建了第一所非神学院体系的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仍是美国第一流的名牌大学。十九世纪,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员计划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Babylon)探险并求大学开专来保存探险获得的古物,宾夕法尼亚大学事会欣然接受这一提议并于1887创建了宾大博物馆。宾大博物馆于1887年年底开始了对巴比伦尼普(Nippur)遗址的探险,从而掀开了长达百年的考古发掘史。首次的探险便为博物馆带来了大批刻字的泥块与其他重要文物。随后,博物馆探险队的足迹遍及了世界五大洲,曾与大英博物馆联合发掘了轰动世界的今伊拉克境内的乌尔(Ur)皇家墓地;参与埃及的考古收获丰硕;在中南北美的探险卓有成效;在希腊克里特岛(Crete)获得了重要的爱琴海文物,等等。一百多年来,宾大博物馆共派遣了350余支探险队,至今仍有专业人员在10余个国家与地区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宾大博物馆的馆名几度更改,但通过考古与考察来研究人类历史的宗旨始终如一。
1911年初,查理斯•哈里森博士来到了博物馆。哈里森博士(Charles Custis Harrison)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卸任后致力于宾大博物馆的发展事业。哈里森生于费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赴哥伦比亚、普林斯顿与哈佛大学深造。毕业后进入商界,因经营制糖业而发财致富,1892年从担任三十年的富兰克林制糖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引退。1894年至1910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建树甚多,宾大校园内至今仍竖立着哈里森校长的铜像。来到博物馆不久,他担任了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长并承担了艰巨的集资任务,其中包括建造圆形陈列大厅、探险与藏品征集所需的费用。他是费城地区资深的政治家、教育家和企业家,他以个人的威望和献身精神为博物馆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哈里森博士的到来使宾大博物馆馆长乔治•高登博士(George Byron Gordon)如虎添翼,博物馆决定扩建并增添陈列大厅。哈里森负责集资,高登馆长主管陈列大厅的展品挑选与陈列工作。高登博士是加拿大人,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主攻考古与人种学,曾任哈佛大学中美洲可庞(Copan)遗址的探险队队长。1903 年起,受聘于宾大博物馆任美国部主任,1910年晋升博物馆馆长他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对博物馆藏品征集具有独到见解,宾大博物馆的现有藏品优势基本在他的任期内形成。
博物馆计划建造的陈列展厅高110米,宽110米,全砖结构,为圆形无柱穹顶,至今仍是美国最大的独立无柱厅。在这气势非凡的圆形建筑内陈列任何展品都是一种挑战,高登却以锐利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决定在此大厅陈列当时尚未普及欧美的世界古文明之一的中国文化。他筹划的圆形大厅的揭幕展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艺术大展,展览于1916年2月揭幕,展品价值百万美元。展览会上除了少数藏品由博物馆购置外,其余大都为借展品。高登还别出心裁地邀请世界各大中国古董商参展,要求他们精心挑选参展品并标明价格,以便参加开幕式的慈善者自由挑选,认购捐赠。这一创新的做法,当时尽管褒贬不一,高登却成功地使绝大部分参展品先后被认购,成为宾大博物馆的固定收藏。正是由于圆形大厅的中国艺术展使高登与卢芹斋走到了一起。卢芹斋(1880-1957)原籍浙江,祖上世代官运亨通,家境富裕,后因太平天国战乱,家产被毁,全家迁至上海。卢于1900年左右来到巴黎求学经商,初抵法国时为求生存无奈去做门房,后在同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提携和投资下,卢与几位驻巴黎的中国使馆人员一起开办了通运古玩公司,经历了开业初期的艰难岁月后,相继在巴黎、北京、上海和纽约开设了来远公司。在此后五十年内,中国古董包括陶瓷、绘画、青铜及雕刻通过他源源不 断地流入欧洲与美国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高登馆长与卢芹斋的交往始于1914年,那时卢首次来美开拓生意,也有可能是应高登馆长参展之邀请而来。高、卢首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卢同意出借绘画、瓷器和雕刻品参加圆形大厅的开幕展,此外,卢还带来了响堂山八尊北齐石雕像的照片。这些石雕的后面有着一段故事:1909年春天,卢在一巴黎博物馆馆长那里见到了一帧石雕像照片,照片上精美的石雕触发了他开辟新生意品种的念头,那时他主要经营清代瓷器。卢立即照片邮寄给国内的合伙人并接到回复说,法国商人马塞尔•宾(Marcel Bing)不久前去西安当地进货,不小心踩到了桌下的石像头。他当场花10元钱买了下来,转手卖给了布鲁塞尔斯道克来收藏(Stoclet Collection),卢看到的就是这个头像的照片。几个月后,卢接到合伙人的电报说搞到了八尊真人大小的响堂山石像,但卢不知如何脱手石像,就叫他们在中国处理掉。但因在当地处理不掉,石像还是被运到了巴黎,巴黎的古董商对这些石刻没有兴趣。卢把石像的照片撒遍了全欧洲,但几年过去了,仍无人问津。卢这次来美想碰碰运气,高登馆长见过这些照片,表示喜欢石像,并愿意通过卢购买,高登馆长的回答自然令卢又惊又喜。他俩都认为收集中国石刻意义非凡,达成共识后,高登当场拍板买了三尊开了宾大博物馆收藏中国石雕的先河。卢也因此决定在美开辟销售雕刻的新市场,高、卢携手合作后还达成了一种默契:以后凡有石雕,卢大都先让高登过目挑选。因此,宾大博物馆的石刻收藏虽为数不多但精美绝伦,遐闻于美国甚至世界。正是有这种合作的基础。卢很自然地把昭陵两骏首先介绍给了高登馆长。
二、昭陵两骏入藏宾大博物馆之始末
据宾大博物馆档案室所藏资料记载,高登馆长于1918年3月9日在纽约首次见到昭陵两骏。3月13日他致信卢芹斋:“上星期六,您的助手带我参观了大都会仓库并见到了两匹石骏。我十分 高兴能见到这著名的雕刻,得知它们在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我会从博物馆角度提出一个最佳方案,与我的同仁商讨购买的可能性。”随后一个月的通讯往来大都围绕着两骏的照片、陈列方案和铸模之事。4月19日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议记载:“馆长汇报卢芹斋愿意将来自古都西安府的两块深浮雕免费借展于我馆。”以借展的方式最终达到购买的目的是高登馆长1916年圆形大厅开幕展时使用的策略,这已成为了高、卢之间多年合作的常用手法。
两骏于1918年5月8日抵达费城。5月7日来远公司一雇员致函高登馆长:“今日用卡车运出了两块浮雕,计划明日中午抵达费城,望一路平安。随函附上照片二套,我们将马的碎块一一编号,相信你们在拼合时不会有什么问题。”从中得知,两骏运输时为碎块,是宾大博物馆布展时才拼合复原的。卢芹斋是生意人,在钱方面是很料明的。他提议宾大博物馆“支付140美金的运输费,此费用可在贵馆购买它们时予以扣除”。他绝不希望因出借昭陵两骏而使资金搁浅,从卢的11月25日信中得知,卢想通过高登馆长向宾大博物馆的银行借款,结果未遂其愿。恰在此时,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派人去见了卢。11月28日卢致信高:“罗斯博士(Denman Waldo Ross)昨日来见我,他受任使用哈维•韦宙先生(Harvey E. Wetzel)的遗产为波士顿博物馆挑选艺术品。他表示只想要一块浮雕,哪怕是不带人的那块足令波士顿博物馆满意。我想贵馆能否放弃其中之一,让波士顿博物馆购买不太重要的不含人的那块浮雕。这将对我极有帮助,我能用他们的资金即刻再为您去购买其他两块浮雕来作补偿。我相信您不会认为我故意从贵馆撤回珍贵的艺术品,我对贵馆的感情始终一如既往,坚贞不渝。”这封信犹如催化剂,迫使宾大博物馆不得不对两块浮雕的何去何从作出明确的答复。那时邮件来往频率之高简直难以令人置信。高馆长11月29日就将卢11月28日函转发给时任董事长的哈里森博士:所附函件自身已足能说明问题。我希望明早能与您见面,只要您愿意,其他董事也可参加,一起商议这一重要事宜。竞争在我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原因之一是这些浮雕自七世纪以来,一直出现于历史记载,证明了中国人视其为艺术领域内的优秀作品。它们是非宗教、纯世俗艺术品,对我馆佛教雕刻收藏能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因为中国早期雕刻是宗教的天下,六骏因而成为稀世之宝。这些石刻实为独特的不朽之作。”宾大博物馆董事会慎重地讨论了此事,商议结果反映在高登馆长12月6日致卢芹斋的信中:“鉴于我们最近的对话,我现作如下声明:经董事会批准,一旦资金落实我们即购买陈列于本馆的唐太宗两骏,现已批准开始筹集资金。如您所知,我馆有现金购买的死规定。由于我们必须筹足15万美元才能购买两骏,上述声明不能被认作是一种合约,但我个人可以向您保证,我们能在明年1月底前落实资金并付清款项。”卢的回复也极其迅速,第二天就通知高登,感谢回复并将他的惠函保存人档。没过几日,卢来信催问,“能否在1月 15 日缴款?因在那日我急需部分资金。”由于卢的催促,董事会又召开了会议,强调了“无论从艺术还是历史角度,两骏都具有头等重要性。极力推荐宾大博物馆尽力购置这对浮雕。”卢期待着高登馆长的诺言兑现,1919年1月3日他再次要求高登在1月 15日付款。看来宾大博物馆的集资进展并没有像高登馆长保证得那么顺利。高、卢不得不考虑其他缓兵之计,高登馆长在1919年1月17日的董事会上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用2万美元购置中国镶嵌青铜器,换取两块浮雕继续保留原处,供我馆以15万美元考虑购置。我馆有权退回青铜器并用2万美元退款抵冲浮雕价款。”哈里森博士于1月28日以书面形式通知高登馆长肯定了这一方案。他说:“我的想法是以2万美元现金购买青铜器,只要卢同意不向他人销售现在我馆的石骏,允许我们在1920年4月1日前或再长时间考虑购买事宜。如果我们能在1920年4月1日或之前以15万美元购置两骏,我们有权归还青铜器,2万美元的退款用以抵冲购买石骏的15万美元,我们若能同时购置青铜器和两骏,则为皆大欢喜。”看来,2万美元的现款暂时解救了卢的燃眉之急,宾大博物馆也争取到了15个月的筹资时间。为了力争哈里森博士信中所提到的更宽裕的时间,卢、高之间的信件往来更为频繁。其实,两骏并非当时惟一的洽商内容,其他文物的买卖也在交叉进行。这就为高卢之间的谈判展现了更大的舞台空间。卢3月12日致信哈里森博士:“鉴于贵馆购买价值五万美元的三只钧窑器以及1919年2月1日2万美元购置了镶嵌青铜器,在此,我允许贵馆在1921年4月1日前,以15万美元考虑购置中国的两匹圣马。我同意在1921年4月1日前不再与任何个人或机构洽谈两骏的买卖问题,给予贵馆自由的无任何限制的购买选择,而没有购买之约定。我对两骏保留在贵馆不负责任何费用,但承担风险。”在之后一年半断断续续的通讯往来中,卢多次探询筹资结果并催促宾大博物馆尽快了结这笔生意。期间,卢同意接受宾大博物馆提出的支付国家债券的方案,但不知何故半年后仍未有结果。高登馆长在1920年6月18日董事会上特别提请大家注意一旦期限来临,其他博物馆已作好购买两骏的准备。我们现处于这样的时刻,要么购买,要么眼睁睁地失去它们。”高登馆长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当时确有好几所博物馆都对两块浮雕虎视眈眈,紧追不舍。卢实在难以招架,不得不告诉急切希望购买浮雕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宾大博物馆“已用信贷购买了两骏”,卢希望宾大博物馆“予以谅解并以同样的口径对外表态”。一些博物馆得知没有希望购买两骏后,则要求提供模制品,在获得宾大博物馆同意后,卢曾向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的吉美博物馆汇寄了两骏的石膏模制品。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宾大博物馆仍无马上结清这笔生意的迹象。卢芹斋故伎重演,建议宾大博物馆购买其他暂借品以解救其资金困境。高登馆长断然予以拒绝,“筹资购买两骏为第一重要,我已通过增收减支的方法来筹集必要的款数,其他文物的购买暂且搁置,直至购买两骏的款项全部到位。”显然,1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捐赠者不愿为陌生的石刻掏腰包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从1918宾大博物馆始1920年10的两半内,宾大博物馆花了不少精力筹资,效果却不显著。不过,多年的力没有徒劳,转机终于在192节夕降临1119议记录写道“经高登馆长提议,博物馆向来远公司购买两块浮雕,原价为15万美元。由于来远公司接受国家债券的支付形式,价格已降至13万5千美元。”哈里森汇报说,艾尔德里奇• 约翰逊(Eldridge R.Johnson,1867-1945)已认捐5万美元作为购置浮雕的启动资金。他随后宣读了致约翰逊的信:“尊敬的约翰逊先生: ……为了实现对博物馆来说至关重要的目标,除了您认捐的5万美元,我计划截留所有未支出的捐款和以后几个星期可能募捐到的藏品专款。如果购买两骏的款项仍然不足,我会自掏腰包加以补足。”哈里森博士在集资方面独树一帜,他随身总带着一本黑色的小笔记本,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和场合,他都会像外交家般地进行集资活动,把情况一一记录在小黑本上。他不仅说服别人捐款,自己也时常慷慨解囊,他的绝招是别人认捐5万,他也认捐5万,他的5万常常用来对付数个其他人的5万。天长日久,他个人对博物馆的捐款也极为可观。在这次两骏的集资过程中,哈里森再次表示了自己解囊的打算,同时也成功地说服了约翰逊加人博物馆捐赠者的行列。艾尔德里奇•约翰逊出生于德拉瓦尔州的惠灵顿(离费城不远)。1894年,开创了留声机公司,后与其他公司合并,在他任董事长期间,新合并的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声机公司。在1921年至1933年期间,他曾任宾大博物馆董事会会员,副会长及会长,多次出资赞助对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危地马拉等地重要遗址的发掘,他对宾大博物馆的一系列慈善活动始于对两骏的捐赠。
两骏的购买终于有了进展。1920年12月 11日博物馆行政档案中记载:“购买两骏,支付来远公司5万美元。”卢于12月15日确认“12月13日函及5万美元支票收悉,此为购买两骏的第一笔付款。”第一笔付款的成功似乎是个好兆头,接下来戏剧性的进展更是让博物馆乐不可支。经与卢芹斋商谈,哈里森成功地将购买两骏的价格降至12万5千美金。再有,约翰逊先生决定“捐赠15万美元用作购买两块浮雕……,剩余的2万5千美金用于博物馆探险考察。”宾大博物馆于1921年1月7日支付了第二笔款项33,300美元最后一笔余款41,350美元的支付有中法实业银行的信函为证。至此,购买昭陵两骏的款项全部付清。
由于约翰逊先生的慷慨捐赠,长达三年的购买两骏事宜终于降下了帷幕。博物馆把刻有“艾德里奇约翰先生捐赠”的铜镶嵌在两骏陈列柜的下方以告众人。宾大物馆沉浸在终获昭陵两骏的喜悦之中,但未曾料到购置两骏所引起的误解与谴责会从此伴随着宾大博物馆达大半个世纪。
三、两骏离开昭陵、西安与北京之始末
宾大博物馆通过古董商卢芹斋直接从美国纽约获得了昭陵两骏,这桩买卖完全局限在相距150公里的纽约与费城之间。那么,究竟是谁把昭陵两骏从昭陵、西安乃至北京运出的呢?如果说宾大博物馆当时对两骏离开西安略知一二的话,对两骏如何离开昭陵和北京则是毫不知情的,有关情况是后来才逐渐透露出来的。
宾大博物馆自1897年就开始了出版新征集品的传统。故两骏买卖尚在商议之际,介绍文章《唐太宗六骏》便已在1918年的馆刊上发表。卡尔•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图十)时任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他在文中写道:“1917年秋,当我代表宾大博物馆造访西安府时,听说一位陕西督军意识到石骏的重要性,几年前在离任时携带保存最好的两骏返回北京。”毕士博的说法引起了一位名叫保尔•马龙(Paul Mallon)的法巴黎商人的不同意见。他于1921年6月29日信宾大博物馆,驳斥毕的说法“不正确,相信博物馆有兴趣了解石骏的真实故事。”他说:“1912年,在京的格鲁尚(A.Grosjean,国古董商)想抢在阿道夫•沃什(Adolf Worth,德国古董商)和马塞尔•宾(Marcel Bing)的进货员达尔美达(d’Almeida)之前弄到这些石骏。他派遣了一位名叫戈兰兹(Galenzi)的助手去搞定此事,指示他以最快的速度最妥的方式将石骏运出当地。1913年5月,石骏被运出昭陵。途中,运输队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拦击,珍贵的石骏被推下山崖。残碎石骏被没收并于1917年托交西安博物馆(有残马在博物馆前的照片作证),它们后被售于卢先生和马塞尔•宾,贵馆就是从他们那里购得。我特别适合向贵馆透露此情况,因为我曾希望通过中间人格鲁尚购置石骏,我的大笔先期投资都因石骏被没收而化为乌有。我想你们一定有兴趣了解这段细节,以恢复著名石骏的历史。”马龙的故事令人瞠目结舌,原来他对昭陵六骏也垂涎已久并付出了大笔投资。从信签上看,他拥有一中国印度支那进口公司(Importation de Chine et des lndes,虽然没有指明专项,不过从中国进口古董亦属对口。他叙述的经历尚合情理,情节也没有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大相径庭,还握有博物馆(实为图书馆)前的残马照片。笔者认为马龙的故事不像虚构,有很大的可信性。他提供了不少重要的信息,如去昭陵的洋商名字本来不为人所知,现知是格鲁尚派遣的戈兰兹;马龙还透露了洋商几次活动的时间,尤其是把首次去昭陵盗马的年月说得很清楚。尽管卢芹斋也提到,“石骏于1912年被洋人盗出昭陵”,但马龙的说法可能更确切一些,即1912 年戈兰兹去打前站,1913年5月才将石骏盗出昭陵。但马龙没有说清昭陵六骏是一次还是分几次被盗出昭陵的。他没有或无法说清的问题,我们有其他出处的资料可加以补充。
卢芹斋曾说,“沉重的石雕在运输过程中被发现、没收,被陕西总督占有。”宋联奎《苏庵杂志》“昭陵六骏”和“石骏再志”条目对此有更清楚的记载:“自辛亥后,石骏为师长张云山取其二,移置长安旧督署(俗称南院),然断泐不堪矣。”“乃未几复为某洋商所觊觎竟举陵北所余四石辇之而去,当道者急追之,始璧还。今存图书馆陈列所中。”郗琳在《关于昭陵六骏被盗真相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供了不少资料。现将有些资料转抄如下:“张云山原是陕西的会党首领,陕西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西安光复后任陕西军政府兵马大都督。1912)受袁世凯改编后任第一师师长。1914年(国年)陆章督陕后被削夺兵权,镇守多方设置障碍不许其赴任。…追陆建章督陕后,云山自知不能见容,而位隆财多,未能洁身远引。乃不惜卑躬屈节,伺承颜色,执贽拜门,辇金纳贿,冀得其观心,以图保全。驯至幽忧致疾,终以不起,于1915年(民国4年三。”琳认为《苏庵杂志》的作者宋联奎也是陕西辛亥革命元老之一,1914张云山为同事,所述张云山取昭陵六骏之二移置南院一事,亲历亲见,应当是实录。张云山于1912年3月任陕军第一师师长,1914年9月缩编后改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苏庵杂志》称张为师长,两骏移置西安的时间则应在1912年3月至1914年9月之间。
基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将两骏从昭陵被盗的几个要点梳理出来:(1)去昭陵的洋商是受格鲁尚指派的戈兰兹;(2)最先离开昭陵的不是六骏而是两骏,时间在1913年5月左右;(3)两骏被拦下后,被张云山占有并移置西安旧督署;(4)在1914年9月后至1915年期间,张云山很可能拿两骏去讨好陆建章;或者他失权或死后,两骏被陆建章霸占。
至于两骏何时离开西安,情形也大致清楚。卢芹斋指出:“1915年,前袁世凯大总统下令它们正式移置北京。”郗琳文中说,陆建章为了效忠袁世凯,又受袁克文的委托,庇护盗运两骏出境。毕士博1917年10月在西安见到四骏时,也说到几年前两骏被卸任的总督运往北京。陈重远在《文物话春秋》一书中对此提供了新的线索,“赵福龄,字鹤舫(1881-1936),北京延吉斋老板,与袁家二少爷袁克文结为好友。在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筹建‘袁家花园’时,赵主动向袁克文提出要为花园建造出点力,计划从外地运些奇花异草、怪石古树,需要封条作护,袁府的封条如同‘皇封’,两骏畅通无阻地抵达北京。”以上几种说法大都与袁世凯有关,时间上可锁定在 1915 年。也就是说,两骏是在1915年进京的。
卢还提到了两骏离开北京的时间。卢在1927年的信中说,两骏“抵达北京数月后,由他人转卖给我们”,它们“离开中国已经12年了”。由此推断,两骏在1915开西安进京,几个月后,即被转手到来远公司,同年就离开了中国。
现再来看看两骏是何时抵达美国纽约的。毕士博1917年2月两次到来远公司纽约仓库,声称“没有发现新东西。”对此,我们可理解为毕没有见到两骏。高登馆长 1918 年3月9日在同一仓库见到两骏时,得知它们在美国已有一段时间。据此,两骏极有可能在1917年2月以后抵达纽约。从北京到纽约的海运时间为1-2个月。如果卢没有记住,确定两骏是1915年离开中国的话,那么,1916年两骏在何处?它们会不会先去别的地方(比如巴黎)保留一段时间再去纽约大都会仓库?如果两骏是直接从北京去纽约的话,那么,两骏1915年离开北京的说法就需再探讨了。
至于洋商第二次去昭陵牵走另四骏的问题,宾大博物馆没有任何档案资料可供考证。笔者据上述资料分析,两骏于1915开西安并售于卢的消息一定走漏了出去。格鲁尚得知后必定耿耿于怀,他与其顾客的大笔投资血本无归,倒让卢白白捡了个大便宜既然两骏能作买卖,留下的四骏也未必不可。或者格鲁尚压根儿就在等待第二次去昭的时机。估计是在1陵了四,结果再次遭到阻拦没收。无奈之中,格鲁尚只能将残碎四骏197图照片投资者以作交代。毕士博1917年10月在西安图书馆见到了四骏,作了笔记并照了相,估计四骏已拼合复原。这证实了洋商的第二次昭陵之行不可能是国内流传的1918年,而是1917年上半年或年中。
叙述到此,两骏离开昭陵、西安北与达约的情况已基本清楚。但与两骏密切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尚未提及:究竟是谁把两骏转卖给卢芹斋?
四、谁把两骏转卖给卢芹斋
在谁把两骏转卖给卢芹斋这个问题上,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可归纳成以下两种主要说法:一种说法是把矛头直接指向袁世凯或以袁世凯为首的最高领导;另一种说法认为是不法古董商的个人行为。第一种说法主要来自卢芹斋,卢1927年9月10日致信哈里森说:“1915年,前袁世凯大总统下令它们正式移置北京。数月后,两骏通过他人售于我们。”卢强调说:“这桩买卖是绝对合法的,这些石骏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出售给我们的。”这是卢从俄国寄至宾大博物馆信中的解释。原来他遇到了麻烦,他的朋友从北京打来电报通知他不要返回北京,因“非法出售唐太宗两骏,北京当权要捉拿我”,卢因此向宾大博物馆透露了两骏买卖的秘密。他还说,“两骏离开中国已有 12 年了,期间没有人怀疑两骏买卖的合法性。我出入北京多次,政府也没有盘问过我”,他认为这不是“政府的行动而是某个人的报复”。据卢说,他曾把一位盗用公司大笔款项的原巴黎古董店雇员送进了监狱几个月,而此人现是外交部官员,想利用职权来陷害他。卢发誓“一定要弄清此事”。
笔者从另一间接出处得知,卢为最高领导出售两骏是“为了集资办学”。卢的继承人法兰克•卡罗(Frank Caro)进一步说:“卢信之将售马金额数交给中国,连手续费都没有收。”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卢芹斋或卡罗所说的“集资办学”的原始信件来进一步佐证。但如果把上述说法合起来看,倒可以引申出对“最高领导”的解释。
卢芹斋指名道姓地把调遣两骏进京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袁世凯。袁是否亲自下令,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赵鹤舫通过袁克文弄到了袁家封条和陆建章为了效忠袁世凯拱手送骏进京的说法都属实的话,这证实袁世凯的旗帜足以达到调遣两骏之目的。卢紧接着说两骏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出售”给他们的,这就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是袁世凯出售了两骏如果袁真是出卖两骏的罪魁祸首,卢为何不直截了当明说呢?1927年时袁已死了十余年,卢点明了袁调遣两骏进京,已没有必要再为袁遮遮盖盖,卢笼统地指出是最高领导,会不会事出有因,出售两骏牵涉到部门而不是个人?如果出售两骏是为了集资办学,不管是真还是幌子,这种说法与上层部门或机构挂钩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分析另一种认为是不法古董商个人行为的说法。根据陈重远先生提供的情况赵鹤舫把两骏运至北京后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它们转卖了。笔者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认为可能性不是很大。两骏进京之事涉及到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与陕西督军陆建章,赵鹤舫想蒙过这两位上层人物实属不易。万一此事被戳穿,带给赵的后果不堪设想。再者,即使赵鹤舫打出“最高领导”或“集资办学”的旗帜来出卖两骏的话,他若能欺骗别人,也未必能骗过卢。因为张静江的关系,卢与上层关系密切,这层纸一捅就破。就算卢不闻不问,但多少也会有点心虚。他一则难以写出“这桩买卖是绝对合法的”铮铮之词来唬弄宾大博物馆;二则也难以逃脱1927年的“陷害”事件。宾大博物馆档案中没有记录“陷害”事件的进展情况,显然卢没有被中国政府监禁,仍旧出人北京,古董生意依然兴隆。卢的化险为夷是因为政府不查下去还是查不下去?仔细分析卢所说的话,两骏是“通过他人售于我们”、“这些石骏是由中国最高领导出售给我们的”,卢很有可能意指两骏出售既有中间人也有后台。中间人是谁?卢没有指名,马龙在信中提到了石骏“后被售于卢先生和马塞尔•宾”,事实情况是两骏都到了卢的手中,马塞尔•宾作为中间人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他或多或少参与了此事,并不影响整个事件的发展。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赵鹤舫充当中间人的可能性最大。在中间人和“最高领导”的问题上,笔者的疑问多于答案。起鹤舫借用袁的势力从陕西牵两骏到北京后,会不会时值全国人民竭力声讨袁的皇帝梦“袁家花园”一事搁浅,两骏处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境地?“最高领导”会不会指上层有关机构或部门?“集资办学”会不会是那时采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和一箭双雕的伎俩?换句话说,赵鹤舫或其他中间人会不会得到高层机构或部门的指使或支持而将两卖给卢芹斋?集资办学有没有先例?卖马的钱是否最终交给了中国政府?如果高层领导没有参与此事,卢凭借什么来捏造这些借口?上述疑团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国内外有关资料予以解答,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一重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两骏由谁卖出的问题虽然有待进一步研究,就像两骏离开昭陵、西安和北京一样,与宾大博物馆并无直接的关联。那么,为何几十年来毕士博和宾大博物馆一直被指责为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盗”呢?据笔者分析,这是由于毕士博多年在中国考古探险而引起的一场误会。
五、毕士博与宾大博物馆的探险活动
毕士博于1881年7月12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是美国派往东京的传教士,毕在日本渡过了童年和青少年。1898 年回美国学习,1912年从德鲍大学(De Pauw University)毕业。1913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参加了哈佛大学皮博德(Peabody)博物馆探险队赴中美洲考察发掘,1914年被高登馆长召至麾下,在任宾大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四年多期间,毕士博曾两次赴华探险。
第一次探险历时16个月(1915年1月至1916年5月)。毕士博先在日本停留半年,1915年8月底抵北京,12月初到重庆。在四川考察时,恰逢蔡锷将军组织云南护国军起兵讨伐袁世凯,在四川与袁军激战。毕经历了不少险情,乘坐的小船还差点沉没长江,他死里逃生,于1916年5月中旬返回费城。各界报纸纷纷刊登了毕士博在中国遇险及平安而归的消息,他的第一次中国探险考察了四川地区的文化遗迹并为继之而来的宾大探险规划作准备。
第二次中国探险始于1917年3月。这次,宾大博物馆规划了中国古都西安的三年探险计划。1916年下半年始,毕积极地为第二次中国探险在作准备。他于12月7日拜访了民国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博士,向顾介绍了宾大博物馆为介绍中国古老文化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出版刊物、系列讲座、考古发掘及收藏陈列。毕邀请顾来馆讲座并提请中国政府对宾大博物馆考察探险活动予以关心与合作,顾大使保证以他在中国的影响极力推荐宾大博物馆。还接到了民国政府驻纽约总领馆热情的来信,支持宾大博物馆的探险规划并通知他的行李仪器设备可免税进关。1917年2月,宾大博物馆正式对外发布第二次中国探险的消息。毕于1917年3月 12日离开旧金山,在横滨停留了二个月后,于5月26日抵达北京。他忙于会见朋友,了解内地情况,时次遇上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张勋于那年6月率领“辫子军”入京,阴谋复辟清室。这场闹剧于7月12日结束,毕却因此损失了不少宝贵时间。后又因水灾冲垮铁路,迫使毕于10月初仍滞留北京。他10月2日给高登馆长汇报说,中国形势不稳定,给美元与中国元的兑换带来了极大的波动,这意味着他的探险预算至少短缺百分之四十,同时他的信用贷款只能维持至9月底。尽管洪水冲断铁路,但他还是准备去内地,他为此还向中汇银行透支750美元。毕一路辗转,终于在1014日傍晚抵达西安府。毕在10月18日向高登馆长汇报了他四天的参观活动,声称他喜欢陕西当地人,陕西是发掘的好地方,他至少需要6周至8周的时间对周围进行考察。毕在10月30日再次致信高登馆长,憧憬着冬季不回美而在当地考察,明春即开始发掘的美景。他进一步肯定了对陕西一带进行大力发掘的重要性,认为渭水盆地是中国的文化根源,如同西方世界眼中的埃及和巴比伦。毕10月18日与10月30日的信件尚在太平洋上漂泊,而他10月2日的信已在宾大博物馆领导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哈里森博士向高登馆长表示了对毕十分不满。毕被第一次派往东亚达16个月之久,理应为第二次中国发掘作好了先期准备,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毕还未到达考古目的地,且预算又短缺百分之四十。毕的毫无实质性的考古进展激怒了馆内领导,他们认为纵有多种不利因素,如毕早日离开日本到中国并立即出发去西安,他就能避免中国的战乱及洪水冲垮铁路等不利因素。他们怪罪毕办事拖拉,缺乏责任性,把博物馆三年发掘计划白白浪费了一年。哈里森博士无法向中国探险资助者交代,更不会为毕再去增集百分之四十的探险资金尤其是当时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紧缩时期。于是博物馆决定召回毕,哈里森博士11月21日电报告毕,“中国探险停止,速回美。”这一决定出乎毕的意料之外,他于12月15日离开北京经日本返美。自从这次中国探险流产后,宾大博物馆再也未能与中国重续考古因缘。
毕于1918年3月初回到宾大博物馆后,大都在整理二次东亚探险的资料。档案中未记载他参与两骏的购置事宜。他在1918年年中开始半脱离宾大博物馆,年底正式离任。弃笔从戎两年余,任美国海军中尉和驻华海军助理武官。1921年和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考古教学,从1922年始受聘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东方部副主任直至1942年逝世。在为弗利尔艺术馆服务的20年中,他在中国考察达9年之久,完成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
由于毕士博代表宾大博物馆两次赴华探险,每次都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1923年以后,毕又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在中国考察发掘达9年之久。他多年在华活动,必然为很多中国人所知道。当得知两骏最终到达宾大博物馆后,人们很容易把毕广泛的串联活动、对文物的兴趣以及在陕西的探险同两骏被盗联系起来。加之格鲁尚派遣的助手是外国人,中国人很可能没有分清外国人的名字而将戈兰兹和毕士博混为一人,张冠李戴,这恐怕是一场误会。毕士博虽未参与两骏被盗的活动,但他191710月18向高登馆长报见到昭陵石骏的提法仍值得探讨。毕有写日记的习惯并定期书面向高登长汇报中国之行。现将毕对有关两骏在日记与汇报中的叙述对照如下,他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10月15日,参观省博物馆/图书馆,金先生电话通知该馆特别安排接待我们见到了少量但精美的魏隋唐雕刻,还有一些不错的青铜器,同时也见到著名的唐太宗六骏中的四骏,都受损严重。后去午餐……。”毕向高登馆长汇报,有时采取报告形式,有时则摘录日记,1917年10月10日的信,他采用了日记的形式:“10月15日,上午拜见了省对外文化专员金先生和……;后去省博物馆/图书馆,见到了不少精美的青铜器,包括当地出二的2英尺高的铜鼎;也见到了著名的唐太宗六骏浮雕,现存四骏,最好的两骏由前督军盗走,它们十有八九迟早会在美国市场上出现。后去午餐……。”
对照之下,毕在汇报中多写了两句,即“最好的两骏由前督军盗走”与“它们十有八九迟早会在美国市场上出现。”有人认为毕所谓的“会在美国市场上出现”的说法纯粹是信口开河,个人推断。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解释。这两句话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两骏被移置北京可留在北京,不一定出现在美国市场。这两句话的添加决不是毕的“画蛇添足”而是有其用意的。正是这两句话,笔者猜测毕在1917年6-9月逗留北京期间,已经知道两骏在卢的手中。根据如下:第一,笔者仔细阅读了毕1917年的日记,毕与卢在北京至少有三次联系,6月9日毕致信卢安排约见,8月19日与9月14日毕又两次写信给卢,是否约见以及信的内容不详。但从中可知,毕有可能与卢面谈或去北京来远店而得知两骏的情况。第二,即使没从卢处得知两骏,毕因在北京逗留数月,广泛接触各界人物,而这些人又大都对考古文物感兴趣,只要两骏到过北京来远店,风声必然透露出来。况且格鲁尚1917年第二次败走昭陵肯定会流传开来,毕多少也会有些耳闻。第三,毕既然肯定两骏迟早会在美国市场出现,也间接证明了毕得知两骏在卢的手中。北京古董商云集,不乏法国商人、德国商人,毕认定两骏会在美国市场出现,这就基本排除了那些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法德商人。卢的商业中心虽然也在法国,但根据前面说到的高、卢之间的合作和新开辟的美国石雕市场,卢一定会把两骏销往美国。只要两骏抵达美国,宾大博物馆必会捷足先登。毕的预测也反映在他的行动上,他在西安曾两次参观省图书馆,他还写道:“在我参观之际,一位有中国绅士风度的学者为我研究四骏和拍照提供了所有的方便。”毕对四骏的特别注意,又是笔记又是照相,看来是有针对性的。毕非常清楚宾大博物馆的规定,凡新征集品都需在馆刊上发表,两骏一旦入馆,写作任务必然落到他的肩上,他有先见之明,已在为撰文作准备了。他不但自己着手准备,也没有忘记通知馆内领导。他在给高登馆长的信中增添了两骏“迟早会在美国市场上出现”的话,貌似猜测,实际上很可能是在为高登馆长通风报信,让他有思想准备,注意两骏在美国市场的出现。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毕士博真的是向高登馆长预报两骏即将在美国市场上出现,这决不说明毕士博或宾大博物馆与偷盗两骏或唆使两骏离开西安与北京的活动有必然的联系。笔者翻阅了毕两次起中国探险的全部日记,除了上面已谈及的,均未发现毕同宾大博物馆对两骏有其他任何动的通信往来。
中国人对失去昭陵两骏痛心疾首,然而痛定思痛,我们还需客观地对待历史事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各大博物馆的大部分收藏都是通过探险考察而征集或直接向古董商购得。对这些征集活动的合法性和道德性的评判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是非标准来衡量。相信历史迟早会对这些征集活动作出公正的评价。希望两骏流失真实情况的公开会有助于我们持客观谨慎的态度和全面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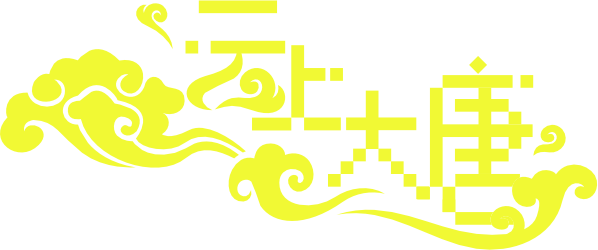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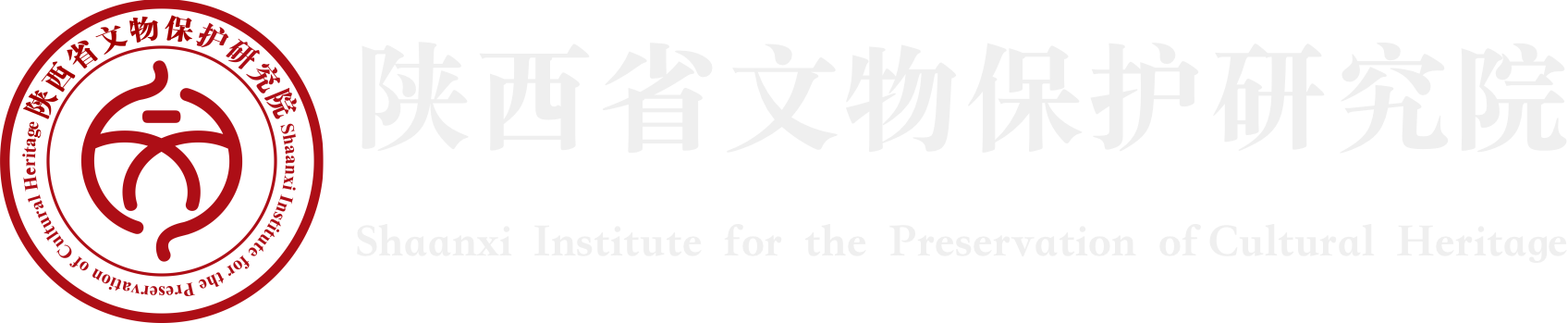




.png)
.png)

.png)
.png)
.png)


骠,高1.74米.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