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详情
PROJECT DETAILS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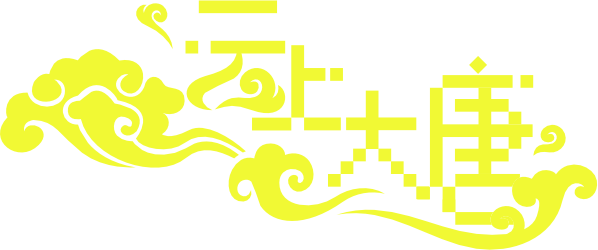
项目概况
团队介绍
媒体报道
主页 >> 新闻 >> 项目概况 




唐十八陵文化遗迹,在原址尚存500余座大型石雕,随着历史变迁,这些矗立在旷野之上珍贵的文化遗产,多数正面临酸雨侵蚀、盗贼扰掠、农用耕地的进一步蚕食,加之位置偏僻难以科学保护及旅游开发,有的已经到了濒危、以致消亡的境地。现急需抢救性运用数字图像、区块链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真实、完整的数据库建设,并通过互联网+艺术+科技的多种新媒介方式,向全世界传播这些经典的中国文化,有效提升传统文化的负载量,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良性发展。同时,通过数字化传播赋予唐陵雕塑艺术“新生命”,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党的十九大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为阐明“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全新模式,更为研究开发、永久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遗产找到了一条最佳途径。
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到来,给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与精神信仰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我们面临“精神价值”重塑的重要使命,这种诉求推动着我们追寻自有的民族精神。而唐陵雕塑艺术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文化思想及民族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洪流中所能展现的优秀品格与智慧,因此唐帝陵雕塑艺术数字平台的建立势在必行。平台利用新媒体技术吸引年轻观众主动地去接受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的唐陵雕塑艺术,增强了传播方式的时代性与互动性;为群众打造一个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唐文化的空间场域,打破了传统展示形式的束缚,能更好、更快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相关研究获奖





专家评介
中国艺术考古所所长、西安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周晓陆:
今天的西安,唐代时称为“长安”,是当时世界东方大帝国的首都。长安南有秦岭屏障,北踞北山耸峙,渭河贯流其间,留下沃野“渭河谷地或称为“渭河平原”,号为“八百里秦川”,自古被视作“陆海”,气候佳尚,物产丰饶,诚中华文明之源渊,民族文化之奥区,西周以降更是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所在,在李唐之际又一次达到了辉煌的高峰。在渭河以北,北山以南,背山面水,西自乾县,跨礼泉、咸阳、泾阳、三原、富平,东达蒲城,在长逾150公里的范围之内建筑了十八座帝陵,埋葬了唐代的十九位皇帝,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王陵区。
十八座唐代帝陵中,有四座以覆土立家形式矗立于渭北台塬,其他十四座皆因山为陵。它们面向都城长安,子午辐辏,以黄土高原的南唇一一北山(包括梁山、仲山、丰山、檀山、桥山、尧山、石马岭、九峻山、武将山、金瓮山、嵯峨山、紫金山、天乳山、凤凰山、虎头山、金炽山、金粟山等等)作雄伟援靠,以泾河、渭河为东西舒缓引带,组成为一个磅礴无比的历史地理扇面。
这批帝陵依托北山,俯瞰泾渭,放眼长安,极目终南;每座帝陵宫墙环卫、殿阙俨然,司马道如箭,隧道玄宫通幽,仿佛地上都城重现;多座唐陵,有文武重臣、嫔妃仕宦陪葬拱卫,生死君臣同在;大部分唐陵四门处有成对石虎、石狮,司马道两侧、陵前都有礼制性、纪念性的石刻:华表、瑞兽(天禄、翼马、獬豸、犀牛、羊)、鸵鸟、鞍马、马夫、虎、狮、文臣武将,碑碣矗立,雄峙至今;在多座唐陵发现有番曹群像,昭陵还有昭陵六骏浮雕,还曾经设有功臣雕像,造成万邦朝会之盛景。
据记载,这些在唐代长时期地动用了巨大国力的营造,直可以看做是当时的一个巨大的集体“行为艺术”;同时,它与周围的山川景观象很好配合,又组成无与伦比的“景观艺术”;更进一步可以看到,这个陵区反映了唐代的从兴盛到哀弱,是一部鲜活的雄伟的“历史场景”。诚如考古学家周俊玲教授曾经指出,这些帝王陵寝,为一个时代社会生产力之集中积淀,是当时物质文化的浓缩美化,实际上超过了散见于当时生活场景、现在一般遗址的常见存在(见《建筑明器美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因此,“唐十八陵区”为后来的世界留下了一个非常壮丽的唐代的文化遗产。
人们在面对这一大片皇帝陵区的时候,心情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古代帝王们动用了巨大的国力,来完成这样一个极为壮观的陵墓寿域,国家财力、民脂民膏,都抛送在山川大地之间,于国计民生何利?!可以说是为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使一个伟大的王朝所能达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辉煌的极致,以帝陵为代表、为托付,完成了固化、遗产化,使子孙后代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得到,并且有可能激励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自从唐代开始,对这些伟大陵墓的记载就史不绝书,有的是以正史的形式,有的是以地方志的形式,有的是以游记的形式,有的是以诗词的形式,更有的是以文物考察、考古报告的形式,记载了这些陵墓。
古代的陵墓再宏伟,古代的石刻再整端,它们总会有消亡的一天。除了社会的人为的原因之外,同时,风化石、浪淘沙,大自然也是无情的,于是就有一个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现代人们如何保护、记录这一笔伟大的文化遗产。
遍揽的想法是正常的,饱尝的欲望源自普通的人,但是因为受到人的个体的局限的制约,个人视力的局限,人们想要看完大地上的唐十八陵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劳动,更不要说进一步的认识与保护了。现在怎么能够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很好很全面的、多角度地看遍、看透,这也是一个问题。
记录也好,饱览也好,根本的问题还是回桓在人们的心中,即这批人类文化遗产的根本价值在于何处,人们今天为什么还需要它们,还想看它们,还要保护它们,还由衷地赞美它们。
上述这三个问题,恐怕永远不会有“终结答案”,可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答。我很高兴地看到张辉教授及其团队,初步完成了国家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陕西唐十八陵数字化保护研究》以及陕西省社科艺术学优秀项目《多维度影像及新媒体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一一以唐十八陵雕塑为例》,在中国国家社科后期资助的及时支持之下,即将奉献出版《唐帝陵石像生艺术研究》这本大著,尽他们之力,做出了卓越的回答。
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这正是“穿新鞋、走老路”。所谓“走老路”就是不断地拓展,在新的时代完成新的认识唐陵的这个就已存在的历史老任务;所谓“穿新鞋”就是在现代用了新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试图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这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体现了这种认识行为和技术考量的一次又一次“空前”性。这样,张辉教授及其团队就从一个角度做出了一些尝试,并且交出了一份令人基本满意的答卷。
这本书从影像学的角度,对“唐十八陵”做出了鸟瞰式的研究,用大数据的形式做了全新的记录。这样,使人们有如锐利的鹰眼从高空俯瞰唐代的陵慕,俯瞰它浩浩然的格局,俯敢它的城垣、阙台、司马道、享堂、玄宫,俯瞰它严整的神兽、翁仲神道。同时,又使人们像勤勉的蜜蜂一样,能够附着在一座座建筑、石刻身上,贴近表面看它们的精工细作,看它们的风化侵蚀程度,思量它们昔日的威仪华丽和干年之后现状之间的差异。这种研究使得今人获得了唐代镌刻工匠、唐代现场臣民的、带温度的感受。应当说他们做了有益的尝试,并且为将来更深入地认识研究唐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新的基础。
从技术和艺术的全面考量来看,魏晋南北朝大动乱之后,唐代陵墓是融汇中西的土石方技术、建筑技术的当时的最高代表,也是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壁画、石刻等等)的当时的最高代表。张辉教授的团队用了超大视角,全面扫视了唐陵这批建筑遗产,又以常人难以达到的角度在空中俯瞰这片建筑。
他们注意到了光线在各个时段,白昼夜间,晴空阴天,雨前雪后,等等不同角度给予石刻的光影关照;他们由机位的拉近、推远、侧观、背视,让人们在瞬间获得从未有过的视觉体验,进而感叹艺术、震撼心灵。我由此想到,对于古代艺术品,尤其是体量较大的艺术品、艺术群体,不应当拘泥于认同于帝王、工匠当时的、定规的创意和感受,应当给予它们以再创意、再塑造。
山水还是那个山水,唐陵还是那个唐陵,像大唐王朝这样的伟大艺术遗产,其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渊薮、艺术的启迪,在未来的时代,会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会再度、数度的爆发,甚至形成原子裂变这样的效果,恐怕这是当时的皇帝与工匠们未曾能够预料到的,这正是古代传统艺术的魅力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优秀的传统艺术达到了不朽。因此,张辉先生及其团队基于先进的认识,做了功德无量的工作。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一千多年以前,这里只是关中大地的一部分,河山依然。由于政治的力量,由于老百姓的辛劳和努力,一座座陵墓次第的拔地而起,组成了这样一个壮阔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的景观。但是多少、多少干年以后呢,由于风雨化蚀、社会性破坏,这一景观又将一点点被湮没,一座座陵墓在此重新沧为沙土。那么,当今人们的认识、研究、保护乃至抢救都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在文物古迹的修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即所谓的“修旧如新”还是“修旧如旧”。这两个观点的争论的关键,实际上就在都没有抓住必须的节点”。如果说是要恢复到刚刚建设的那些陵墓、寺庙、宝塔的样式状态,那就叫必须“修旧如新”。如果说关心的是它被人们重视、收藏保护的某个后来的时间节点,那就叫应当“修旧如旧”。在这里,序文之中不展开对这俩观点的讨论。问题在于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些唐陵的大面积景观、直到具体的建筑、石刻等等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那个时候人们再谈所谓“修旧如旧”的时候,该就是轮到现下的“时间”节点了。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对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批建筑的现状做了一个很好的记录表达,使将来人们不仅能认识它、欣赏它,而且甚至可能保护它、修复它都有了一定的时代“节点”的依据。
张辉先生是西安理工大学的教授,他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科技手段和人文态度的一次充分的结合,这使人们看到了历史文化艺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在这点上,太应当值得赞许。对于人文科学研究它无论研究的怎么深透,它的功能、范围总是有限的;同样的,理工科研究也有它特定的范围和维度。考古学不是全能的,艺术学不是全能的,工程技术科学也不是全能的,如果能够打破各个学科的这些范围和维度,能够把它们很好地融会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成果,就会使人们的眼界大开,进而促使人们“脑洞”大开。
二十世纪60-90年代是一个技术长足发展的时期,置身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恩惠,使人们能够由表及里的更加深刻的了解古代的遗产以及他们的物质材料和技术工程方面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如果人们只停留在文物保护和文物欣赏旅游的范围,那可能是目光短浅的。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存在,将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基础和阶梯,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这部大著的直接研究对象是唐陵“石像生”,这些威严、壮美的人造物群体,沿着人类历史文化大道,一路由古代埃及、古代两河、古代波斯的陵寝、宫庙出发,向着东方蹒跚走来。在泰汉时期到达中土,东汉时期在陵墓前排开,经历魏晋南北朝,入唐而成为中国式的重要“定制”。因此,这部大作就有了“国际意义”,我不认可“唯我独尊、自我孤立”,我乐观并且享受着人类文化艺术东去西来的频繁交流。张辉教授以艺术和技术结合的眼光,向人们展示了即便如盛唐之时,中国也要虚心学习、融入世界的气概。这符合现下所侣导的艺术考古学的学风理念。
说到“艺术考古学”,我定义为“服务于艺术史重建的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张辉先生的工作也可以归诸于“艺术考古学或者“艺术史学”范畴。涉及到“艺术史学”,针对历史艺术遗产,目前大致有两个学派一一“风格学”和“图像志”研究,海外泊来,鸣金擂鼓,剑挥载舞,有时几近势不两立。无论自觉或者不自觉,张辉先生在研究中很好地进行了科学的通融。
所谓的“风格学”研究,考古人可以理解为对于由田野“地层学”收获提供的资料(包括艺术史料),进行考古学的“器物形态学”具体分析:入材料、入技法、入骨,出时代、见方法、见细节、确立“型、式”。张辉教授的团队虽然不及全面,但已经做的很好:那么多表格、局部,进行时空及本体意义上的详尽对比;座座“石像生”本体呼之欲出,打造装饰它们的技术和艺术呼之欲出,唐代的设计者和工匠呼之欲出,此著让“风格毕现”,使人看了大呼过瘾。
所谓的“图像志”的研究,考古人可以理解为考古学在物质遗存群体升华为“社会文化”的探索,“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透物见时代”。张辉教授的团队虽然不及深入,但已经做的不错:他们遥追周秦汉传统,不遗余力地张扬大唐风习,唯活唯志。除了大量文献的再诠释,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此著还以图像为现代“守陵人”几左近的最下层人们代言,表达了一种唐“石像生”艺术的深远的社会性辐射。
张辉先生在他的工作当中注重团队精神,注重年轻人的培养和教育,这是尤为宝贵的。一个人做不完许多的事情,但是通过团队就实际上是个人力量积极的平面延长,这种延长会传至后人成为一种新的纵向传统。
这种形成中的、立体的传统我想就是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新型有机结合吧。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爱以及把这种关爱通过艺术表达,再通过工程技术的方法以更大的、更普遍的延及到悠远的历史传统上,延及到的历史文化遗产上。这样做无疑是对现在的教育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同时时代逼着人们实践着、试图完成、回答这样的课题。所以看他的著作,看到由历史的存在而形成为全息影像,看到由丰富多样的遗产而转换为大数据,看到了由精致洞察而达到了真正艺术与文化上的“穿越”……应当说不由地令人感到兴奋。通过张辉的图书,大家可能能看得更加深远一些,使得唐陵所包含的当时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艺术信息以及所能提供给未来发展的各种参考资讯都能够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
陕西省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历史文物古迹蕴含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张辉教授以及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面对大唐这组最好的历史文化遗产对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文化遗产很好的实践范例。他们工作当中的全部理念以及全部技术手段几乎都可以用到其他文物古迹上去,不论周秦汉唐,不论是地上地下,也不论是石刻还是其他建筑。
张辉和同仁们开创性地搞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研究事业。我希望张辉教授看到大家的好评(包括这篇序言的赞美),会感到“脸红心跳”,因为在历史面前,在未来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孩子、小学生,你们已经走过了让人们兴奋、羡慕的一段,但是前面要准备填补更深的不足,面对更多的艰苦,迎接更大的辉煌。这是你们的系统的研究的第一本报告,希望再次第而来的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越来越精彩,提供越来越多的画面,提供越来越深刻的体验、文字和思考,提供越来越充分的实践的经验,以向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全世界,献上学术的、技术的和艺术的、艺术考古学的厚礼!
在2017年作序时,为表达读后的兴奋,题《浪淘沙》一曲为志:
渭北座如屏。
“吞吐群星,宫垣碣阙再神京。
狮马俨俨驼鸟静,华表丹青。
旧影敢图新。
数据桁楹,精微广大善敷陈。
传统而今同谱唱,再造唐陵!
2017年冬至夜于大雁塔西。”
今天再次看到张辉教授论著叠经修改,更放异彩,又得到国家社科后期资助方面的及时支持,真值得再赋《浪淘沙》为志:
“孔雀展新屏。
挥洒成星,恢弘壮大又西京。埃及波斯已寂静,中夏留青。
汤铸鼎盘新。
图像充楹,旧情新法赞纷陈。大地待君千百唱,何止唐陵。”
项目进度
主页 >> 新闻 >> 项目概况
test
test


专家成员


周晓陆
中国艺术考古所所长
西安美术学院
博士生导师

张建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西北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赵强
陕西省文物保护院 院长
科技部文物保护国际
合作基地主任

王双怀
历史学专家
陕西师范大学
博士生导师

韩建武
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文物保护院
副院长


教师成员


张辉 教授
硕士生导师 项目主持人
西安理工大学三级教授、设计艺术学学科带头人、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国家艺术基金、文化部科技创新等十余项课题。
曾获得国家教育部颁发的指导教师一等奖2项;索尼世界摄影二等奖;分别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颁发的“中国摄影教育优秀教学奖”及“中国摄影教育特殊贡献奖”;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陕西省第十五届哲学社科二等奖;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4届、25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优秀奖;作品入选文化部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获得陕西省两年一届唯一的“陕西摄影奖”等。
4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于《文艺研究》《美术》《装饰》等期刊,出版教材及专著9部。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韩国仁川、中国西安以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等举办个展8次,参加国内外专业展览70余次。
与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慈善协会、西安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组委会、韩国仁川海洋艺术节组委会等共同策划组织大型艺术展览“保持纪录-2017西安国际摄影邀请展”“首届digiartist国际数字艺术展”“首届陕西省大学生摄影大展”“2018从长安到罗马-中意高校邀请展”“2020异域同天-中日韩高校摄影邀请展”“2022微茫成阳-亚太地区高校摄影邀请展”“近景·十年”“挚守传统的涅磐”等。策划组织“冲决藩篱·星星世界”公共教育研究项目获得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优秀公共教育提名奖”。
作品被广东美术馆、美术文献艺术中心、丽水影像博物馆、崔振宽美术馆、陕西汉唐石刻博物馆及个人收藏。

苍慜楠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数字媒体艺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研究。校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优秀本科生导师,本科教学优秀,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等荣誉。发表论文、设计作品20余篇,指导学生参加省部级以上竞赛近30项,指导获奖23项,国家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级优秀结项2项、省部级等级奖18项、优秀奖5项。先后主持: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陕西省艺术学规划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校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8余项横、纵项科研项目。参与文化部、教育部等纵向10余项。
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虚拟现实交互

张妤静 教师
公共艺术中心教师
西安理工大学公共艺术教育中心教师,法国圣太田大学造型艺术研究、艺术家书籍双硕士。论文《无墨之墨--从去物质化哲学到去水墨画》获2012年法国圣太田优秀硕士论文,收录至学校图书馆馆藏。2016、2017年分别担 任《创艺-陕西首届高校中青年教师设计、艺术展》及《画乡-户县农民画新语境》策展人。

董海斌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陕西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剪辑学会短片短视频艺术委员会理事、陕西省动漫游戏行业协会行业顾问、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员、全国高等院校数字创意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教育部、省社科省部、厅局级项目4项,参与军委科技委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7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先后荣获西安理工大学优秀教师,科研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主要进行数字媒体、影像艺术、动画艺术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虚拟现实与交互设计、纪录片创作等。

俞瑾华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Notre Dame、Saint Mary’s College访问学者。多年指导学生参与各项专业设计实践和赛事,被教育部高教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广告协会及陕西省教育厅等单位授予杰出指导教师称号。在文艺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三十余篇专业研究论文及作品,主持与参与多项教学研究项目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研究方向:视觉传达与多媒体设计、品牌广告策划与新媒体传播设计、包装结构与装潢设计、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交互与界面设计。

孙浩章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先后在 SCI、A&HCI、EI、CSSCI、CSCD 等核心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 1 部,参编教材或专著 3 部。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5 项,厅局级科研课题 4 项,其他级别社会科研课题 20余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普通高校省级优秀教材二等奖等多项国内外奖项。主持并完成教改项目 3 项,2019 年入选科研工作先进等荣誉称号。
研究方向:影像艺术与信息设计、视觉传达与新媒体。

王慧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先后赴印尼、加拿大、德国、美国等国家进修学习、考察、参展和研讨交流。主持和参与国家级一般项目、省部级项目 10 余项,出版专著 1 部,发表学术论文 21 篇,其中 CSSCI 4 篇;获陕西省第四届研究生创新成果展优秀指导教师;获批实用新型专利 20 余项,其中第一发明人 11项;兼任中国教育书画协会高等美术教育学会理事、亚洲 AADA 设计奖中国区评委、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设计委德国区域国际设计导师等学术职务。
研究方向:城市空间绿色可持续发展、环境设计与工程应用。

孙茜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摄影学会理事。University of Sussex(英国萨赛克斯大学)访问学者;主持省级课题3项;厅级课题1项;参与国家级、教育部课题4项;主持校级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教材1部;授权实用新型专利5项;获得省级教学能手奖、省级高等教育成果三等奖、校级先进个人、师德优秀教师称号。
研究方向:视觉传达与数字媒体设计、水墨与新材料艺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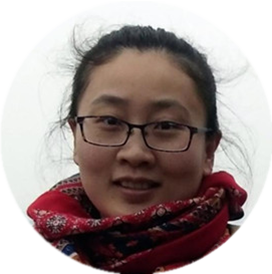
魏琰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1项,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1项,校级科学研究项目3项,横向课题3项,专业教育教学与教材建设2项,参与科研课题10余项。在CSSCI期刊3篇,EI检索1篇,国内会议宣读论文1篇,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9项,参与环境设计专业模型实验室等教学建设项目。
研究方向:人居环境设计、城市规划理论、中西方建筑史

杜杰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2004年获设计学硕士学位,2020年获工业设计方向博士学位,美国著名常青藤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主持国家教育部艺术基金、陕西省教育厅艺术专项基金两项。发表核心论文10余篇。主持横向设计课题多项。并被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陕西省教育厅、中国广告协会、中国包装联合会授予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研究方向:视觉传达与多媒体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程、民间美术研究

王蓓 教师
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
1977年 8月生于陕西西安。西安美术学院设计系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0年至今在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从事本科教学工作。近年来主要研究视觉形象及包装设计方面的相关课题,先后在中国原子能出版社专著《环境保护下的绿色包装设计研究》和教材《包装设计》,同时申请和参与了多个校级、省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分别以作品或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文艺研究》、《中国教育学刊》《包装工程》等国家级A、B类核心期刊,并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各类包装平面设计大赛,取得了多个等级奖和优秀奖的优异成绩。2020年获得校级优秀教师称号。

王玮 教师
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
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动画系教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员。多年互联网和游戏行业从业经验,参与和主持研发《剑侠情缘3》《我的王国》《口袋商业街》《永恒战士》等十余个项目,获得包括金翎奖在内的业内多个奖项,并在美国E3等大会参展,作品在多个国家发行,享誉海内外。从教后有多篇文章、作品发表于中英文专业期刊,并指导学生在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张省会 副教授
艺术设计学院教师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硕士,陕西高校摄影学会副秘书长,现任职于西安欧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方向负责人,数字摄影工作室负责人。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数字影像》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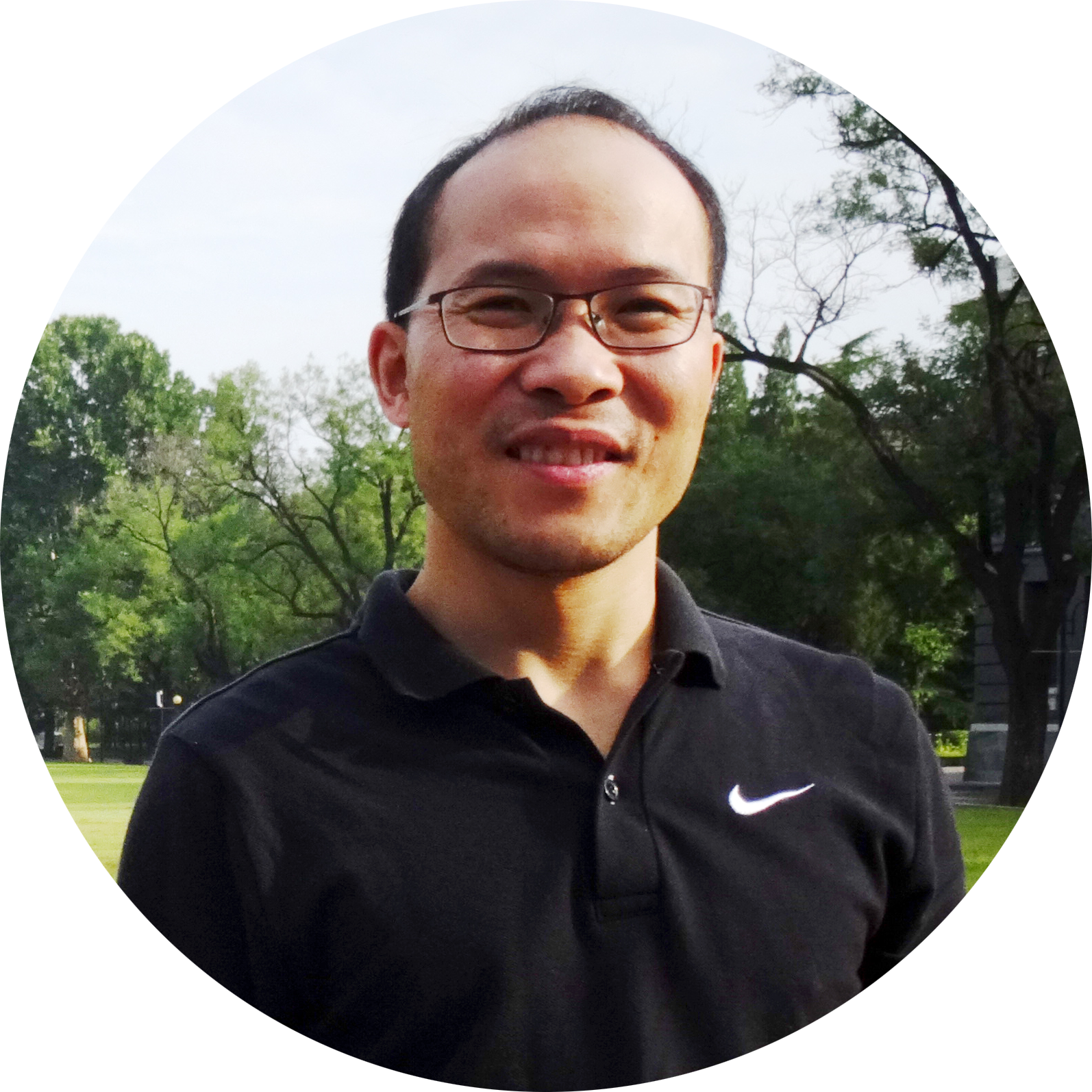
张新平 讲师
高级工程师
生态学博士,讲师,具有高级工程师、二级建造师资格,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中国大坝工程学会会员,多个期刊审稿人。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与遥感监测、景观与水文生态、城市林业与森林康养、数据可视化与科学计量。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SCI 2篇,SSCI 1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国家野外观测站开放基金1项、厅局级课题2项,参与国家级课题多项,获国家林业局科技成果、中国大坝工程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各1项。

孙昕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从事建筑空间环境设计、室内与产品造型设计研究,曾在美国爱达荷大学艺术与建筑学院任访问学者。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项,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项,校级科学研究项目多项,参与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以及企业课题多项。发表SCI学术论文2篇,EI学术论文3篇,CSSCI、CSCD期刊论文及作品多篇,出版专著1部,出版教材1部,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4项。获得西安理工大学优青人才、教书育人先进个人、优秀本科生导师、本科生毕业设计优秀指导教师等称号。

李元
多年来从事艺术设计教育工作,以及视觉艺术、空间艺术设计研究。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获硕士学位。曾赴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访问学者,研究艺术教育心理学。主持省社科项目,并参与多项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以及承接企业相关合作课题多项。发表多篇核心期刊论文及作品,获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任西安市美术家协会漆画艺委会理事。



学生成员


董维
西安理工大学 2018级研究生
负责网站数据库搭建

孙婉
西安理工大学 2019级研究生
负责网站界面UI设计

慕琼
西安理工大学 2019级研究生
负责唐陵石狮交互设计

杨玉叶
西安理工大学 2020级研究生
负责电子书制作

胡敏瑞
西安理工大学 2020级研究生
负责番酋像研究

高帆
西安理工大学 2020级研究生
负责网站对接

王天俊
西安理工大学 2020级研究生
负责纪录片拍摄

王登轩
西安理工大学 2020级研究生
负责720制作

高晓林
西安理工大学 2020级研究生
负责实地调研

孔庆鹏
西安理工大学 2020级研究生
负责三维扫描

贾瑞雪
西安理工大学 2021级研究生
负责三维制作

况文杰
西安理工大学 2021级研究生
负责网站设计与对接

左钰桐
西安理工大学 2021级研究生
负责720制作

侯秀丽
西安理工大学 2021级研究生
负责720制作

吕梦星
西安理工大学 2021级研究生
负责墓室结构交互

汪彬彬
西安理工大学 2012级研究生
负责三维扫描

刘盼
西安理工大学 2012级研究生
负责360度全景制作

翟佳佳
西安理工大学 2013级研究生
负责动画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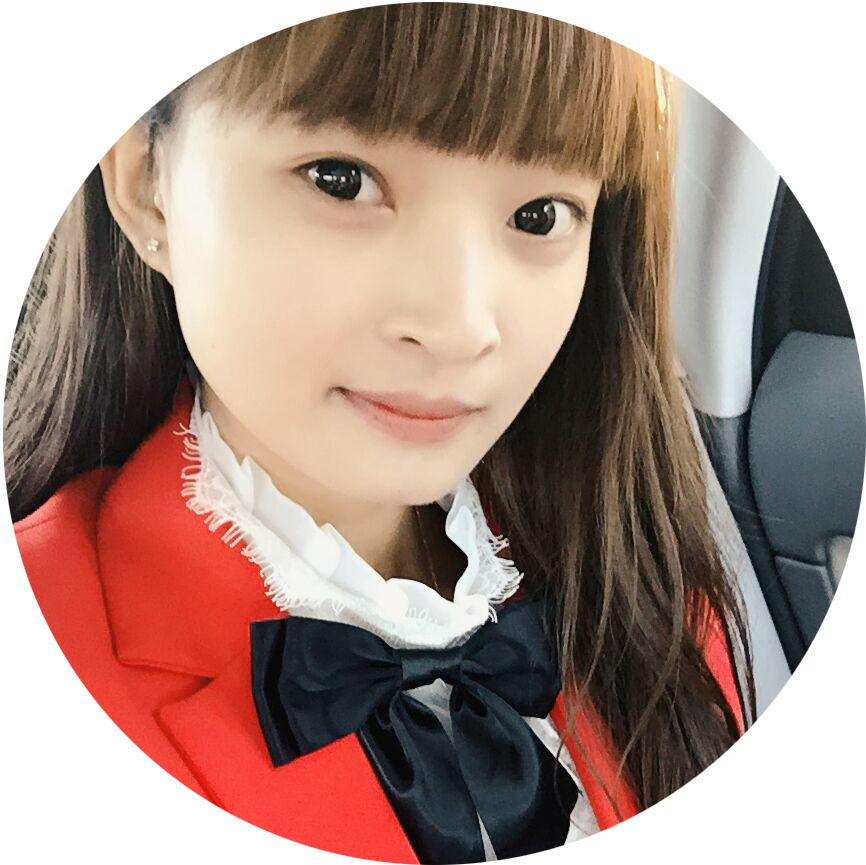
王冬梅
西安理工大学 2013级研究生
负责三维扫描

张超
西安理工大学 2014级研究生
负责三维扫描

张一天
西安理工大学 2014级研究生
负责图片素材拍摄

闫润扬
西安理工大学 2014级研究生
负责H5页面制作

徐云
西安理工大学 2014级研究生
负责纪录片拍摄

李珂为
西安理工大学 2015级研究生
负责三维扫描

樊一霏
西安理工大学 2015级研究生
负责H5页面制作

沈姚姚
西安理工大学 2015级研究生
负责H5页面制作

王怡卜
西安理工大学 2016级研究生
负责唐陵网站设计制作

王硕
西安理工大学 2017级研究生
负责H5页面制作
主页 >> 新闻 >> 媒体报道
![]()


陕西省电视台都市快报栏目
2022年9月27日,陕西省电视台都市快报对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张辉教授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进行了相关报道,这两个项目都是以影像学、艺术学为线索进行对比研究,综合社会学、历史学,同时用现代多媒介和新媒体的方式展现帝陵文化及石像生,力图以此揭示唐代289年间文化相互作用演进的动态图景。


西安市电视台融媒体中心
2022年9月18日,西安市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对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张辉教授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进行了相关报道。这两个项目是西安理工大学深化科研改革,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成果体现。华商网、陕西都市快报、都市时报等14家媒体,也对该项目进行持续报道。


白鹿原视频
白鹿视频、华商网、陕西都市快报、都市时报等14家媒体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进行转发报道,累计总览量高达138.8万余次。






《装饰》期刊专访
2022年4月,《唐帝陵雕塑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研究》在《装饰》期刊在校园风采栏目发表。该篇论文为保护唐帝陵雕塑文化遗产,为研究开发,永久保存和弘扬文化遗产找到了一条优良的途径。








华商报专题报道
2019年6月5日,华商报对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张辉教授及其团队的对于唐陵考察进行了专题报道,其中包括蓝晒唐陵——唐陵的另一副面孔和数字唐陵——3D扫描唐陵细节两个模块,为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新鲜的模式和思路,张辉教授也表示文化传承是人类的使命所在。


三秦都市报报道
2022年11月14日,三秦都市报对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张辉教授及其团队的对“唐十八陵雕塑艺术网络平台”将于12月上线运营,这一数字化保护项目,通过建立综合数据库与创新数字展示方式让唐帝陵雕塑“活起来”。


中国摄影报报道
十数年来,张辉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进行唐陵的考察探究,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引起了中国摄影界的广泛关注,也得到了《中国摄影报》多次的专题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境外宣传专版
2007年至今,团队考察唐陵已有十五年余载,在这十数年来,我们的项目也得到了国内外的支持和关注,国际方面对唐陵也有了关注,澳大利亚以及韩国等其他国家也对我们唐陵的项目进行专题报道。




雅昌摄影专题报道
2007年至今,团队考察唐陵已有十五年余载,在这十数年来,我们在国内获得了大量的关注,雅昌摄影网站也多次对我们的唐陵的项目和团队进行专题报道。




期刊报道
十数年来,张辉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进行唐陵的考察探究,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该项目图片文字在十数种杂志期刊进行专题报道,也得到了《中国摄影》、《大众摄影》、《美术文献》等期刊的的专题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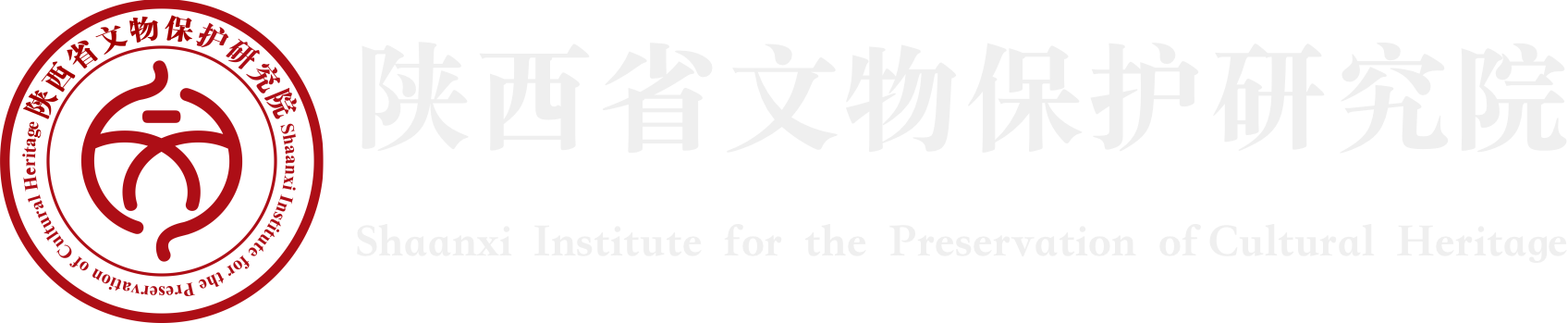
- 技术支持
- 西安旆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慕光科技有限公司
- 特别鸣谢
- 西安碑林博物馆
- 乾陵博物馆
- 昭陵博物馆
- 唐桥陵文物管理所
- 唐泰陵文物管理所
- 唐建陵文物管理所
- 唐献陵文物管理所
- 唐顺陵文物管理所
- 唐贞陵文物管理所
- 唐崇陵文物管理所
- 唐景陵文物管理所
- 唐元陵文物管理所
- 唐定陵文物管理所
已有6012738位访客浏览此网页
版权所有: 西安理工大学 陕ICP备05001616号-1





















